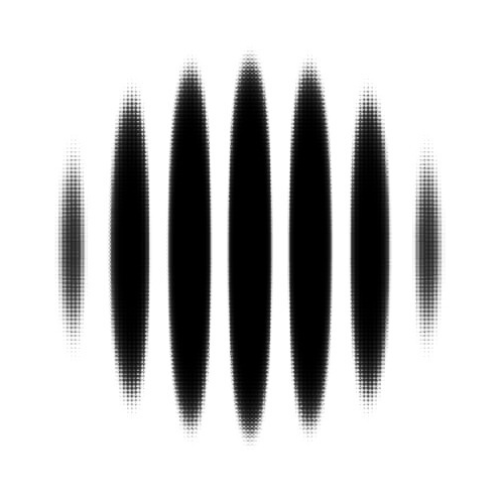多巴胺专家警告:短视频正在“烧坏”你的大脑——这是一场多巴胺灾难!
Dopamine Expert: Short Form Videos Are Frying Your Brain! This Is A Dopamine Disaster!

Dopamine Expert: Short Form Videos Are Frying Your Brain! This Is A Dopamine Disaster!
The Diary Of A CEO|Youtube|2026-01-05
推荐理由
如果你总觉得自己“明明不想刷,却停不下来”,这期对谈会给你一个更清晰、更不自责的解释框架:问题不只是意志力,而是我们的大脑被训练得更擅长追逐“高多巴胺的即时奖励”,在压力、孤独、疲惫时尤其容易复发。
斯坦福成瘾专家 Anna Lembke 用极直观的“快乐—痛苦天平”讲透:为什么越追求爽越容易麻木(快感缺失),为什么 AI、短视频、色情与社媒会把“人际连接”做成一口一口的糖,以及你真正能做的改变是什么——从“4 周戒断/重置”、到设置物理与心理的“自我绑定”护栏、再到“先做难事”的晨间策略。听完你会更像是在拿回主动权,而不是又背上一条新年计划。
作者简介
主持人(Steven Bartlett)
史蒂文·巴特利特(Steven Bartlett)是英国企业家、投资人,也是播客《CEO 日记(The Diary of a CEO)》的创办人兼主持人。他以深度长访闻名,节目在欧洲影响力极大,长期邀请商业、心理、健康与文化领域的一线人物展开对谈;同时他也是 BBC《创智赢家(Dragons’ Den)》的“龙”投资人之一,活跃于创业与投资圈。除内容创作外,他还创办并运营多家与媒体、创作者经济相关的公司,并著有《The Diary of a CEO》等畅销书。
嘉宾(Dr. Anna Lembke)
安娜·伦布克(Anna Lembke)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、成瘾医学(Addiction Medicine)医疗主任,同时担任斯坦福成瘾医学“双重诊断诊所”(成瘾合并精神障碍)负责人,并主持斯坦福成瘾医学专科培训项目。她长期临床接诊并从事研究与教学,关注成瘾、强迫性过度消费以及数字媒介对大脑奖赏系统的影响,尤其以“多巴胺与现代过度刺激”这一公共议题为大众所熟知。她是《多巴胺国度(Dopamine Nation)》等书作者,并在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与成瘾治疗领域有重要影响力。
原文编译
引言
有个很经典的实验:给老鼠一个可以按的杆,按下去就能得到可卡因。老鼠学会“这东西会带来大量多巴胺(dopamine)”之后,会一直按到筋疲力尽,甚至按到死——这基本就是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的成瘾模型。
但如果把可卡因拿走,过一段时间,它们最终就不会再按了。
现在更关键的是:如果同一只老鼠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,又被施加一次非常痛苦的足底电击(foot shock),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过去、重新开始猛按那个杆。
这很有力量,因为它说明:当个体处在极端压力下,他们更容易回到那种强迫性的过度摄取(compulsive overconsumption)——回到自己“最爱的药”(drug of choice)——因为大脑早就把“用高多巴胺奖励来逃离痛苦”编码成了捷径。
好,那我到底该怎么做,才能戒掉坏习惯、再养成一些新习惯?
我们请来了安娜·伦布克医生(Dr. Anna Lembke)。她是斯坦福成瘾诊所(Stanford Addiction Clinic)负责人,也是研究多巴胺的顶尖专家。她回来是为了提醒我们:成瘾是现代瘟疫,以及我们如何重塑大脑、夺回控制权。
一般来说,人们需要 4 周左右,才能从“持续渴求”(craving)的状态里走出来。
但问题是:我们的生存,取决于我们能否学会在“丰裕世界”(a world of abundance)里生活。
比如,我们正在看到“人类连接的药物化”(the drugification of human connection):社交媒体、约会软件、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(AI),都被设计成恭维、肯定、验证你。这里没有摩擦(friction)。于是它把我们从现实里那些更难、却必须去做的事里拉走——那些事才会培养真实的人际关系。
我们不能继续走这条路,因为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,我们正在把自己“娱乐到死”。听起来像个不错的死法?其实不是。因为对快感的无休止追逐,会导致快感缺失(anhedonia)——也就是,你将无法从任何事情里获得快乐。
认识嘉宾
主持人: 安娜·伦布克医生,如果有人没看过我们上次的对谈——那期我个人非常喜欢,Jack 也跟我说那是他最喜欢的一期——你是谁?如果要总结你的职业生涯:你的智慧来自哪些参照点、哪些经历、你与哪些人一起工作过?
安娜: 我是精神科医生(psychiatrist)。我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培训(residency),之后留在斯坦福任教。我看诊、做研究、也教学。
多巴胺与过度丰裕
主持人: 你写过一本关于“多巴胺”这个词的标志性著作。为什么它这么重要?为什么“多巴胺”这个概念如此关键?
安娜: 多巴胺是我们大脑里会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。但在书里,我把它当作一个延展隐喻,用来描述:“过度丰裕本身”其实是一种人类压力源(stressor)。
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:我们拥有更多奢侈品、更高的可支配收入、更多的闲暇时间——甚至对最贫困的人来说也是如此。结果证明,这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压力的,而且是一种全新的压力形式:我们以前从未真正面对过。它让我们更容易陷入强迫性过度消费与成瘾问题。
我确实认为:成瘾是现代瘟疫。我们会在一个丰裕世界里,与强迫性过度消费的问题长期纠缠——以“世纪”为尺度。我们的生存,取决于我们能否学会在丰裕世界里生活。
主持人: 虽然我们的大脑是为“稀缺世界”(scarcity)进化出来的。
如何摆脱坏习惯
主持人: 每到这个时候,人们都在想改变:变健康、减几斤、存钱、戒瘾、戒烟、戒毒、戒酒……就多巴胺而言,它和“习惯”到底怎么连起来?如果我想戒掉坏习惯或养成新习惯,理解你在《多巴胺国度》(Dopamine Nation)里讲的东西为什么关键?
安娜: 起点是自我慈悲(self-compassion)。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丰裕世界里,几乎可以轻易获得各种“强化物”(reinforcing substances and behaviors)。而“可得性”(access)本身就是成瘾最大的风险因子之一。
你在一个毒品触手可及的社区长大,你更可能去尝试,也更可能成瘾。那成瘾性物质与行为对大脑做了什么?它们会在大脑某个专门区域——奖赏通路(reward pathway)——一次性释放大量多巴胺。
而“一次性释放这么多”,意味着它是高度显著(salient)、高度可记忆(memorable)的经历。大脑会把那种强烈快感深深编码:那是我自己给自己“用”的,我未来还能再来一次。
为什么有害的东西会让人上瘾?
主持人: 如果我现在抽一根烟,从大脑角度看,它会成为一次非常“可记忆”的体验。为什么大脑要把它记得这么牢?从“生存”角度讲,为什么我会想再来一次?
安娜: 先区分一下“自然奖励(natural rewards)”:食物、衣物、住所、寻找伴侣——这些是我们为了生存必须获得的。
而成瘾性药物与行为,会通过利用我们大脑内部的化学机制,模拟这些自然奖励:它们让多巴胺一次性释放得更多,远超自然界里的自然奖励。
这会放大体验,让它更难忘、更显著,也会让大脑误以为:“啊,这东西对生存很重要。”
主持人: 所以像吃饭这种自然奖励,我身体当然会奖励我,让我还想再吃。可香烟、威士忌、毒品这些,是人造化学物,被设计来“劫持”那条通路,把感觉放大到让大脑误以为它像自然奖励,但其实是合成的、人工制造的。
安娜: 没错。而且过去两百年尤其明显:科学与技术被用来让“药”更强、更快、更易获得——比如可可叶被提纯成更高效、更猛烈的递送机制。简而言之:药物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容易得到。于是,被劫持的大脑更普遍。甚至我们还把以前不算“药”的东西,也变成了“药”。
AI 正在把“人类连接”变成药
安娜: 记得自然奖励里有“找伴侣”。我们大脑推动我们去做这件事的方法之一,就是让坠入爱河、亲密、人与人的连接,在神经生物学层面“有奖励”——当我们建立社会连接时,奖赏通路会释放多巴胺。
我在斯坦福的同事罗布·马伦卡(Rob Malenka)及其团队做过一个实验:他们发现催产素(oxytocin,“爱情激素”)会与奖赏通路中释放多巴胺的神经元结合,并促使其释放多巴胺。再一次证明:恋爱与人际连接会带来奖励,会让人感觉好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是:人类连接被“药物化”。比如社交媒体、约会软件、网络色情,以及如今的人工智能(AI)与其他大语言模型(large language models)。
这些技术制造出一种无摩擦(frictionless)体验:像在和人说话,而且极其“肯定你”。
大语言模型的算法被设计成让我们感觉非常好——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、增强自尊、验证我们的立场。
更进一步,现在还有明确色情化、明确情色化(erotic)的 AI 模型:它能学习我们喜欢什么,再把它“反刍”给我们。于是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行动—感知回路(action–perception loop):这正是“药”之所以强的部分——因为我能控制它。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改变自己的感受:通过用这个“药”。
主持人: 你担心 AI、大语言模型这些正在模拟人类连接的东西吗?
安娜: 我非常担心。我看到的坏结果包括:人们对社交媒体、约会软件、网络色情、以及 AI 上瘾,结果他们用这些媒介来模拟连接,却在现实中越来越断联。
主持人: 你在门诊里开始见到“对 AI 上瘾”或“与 AI 建立关系”的人了吗?
安娜: 我们开始看到了:一些人花越来越多时间在 AI 上找陪伴。常见情境是:他们正经历婚姻或人际冲突,于是转向 AI 寻求建议,以及寻求情绪验证——因为他们从伴侣那里得不到。
AI 会给予巨量情绪验证:肯定他们的观点,同时提供某种陪伴感——反复让他们觉得“被理解、被验证”。于是他们在 AI 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。
而数字媒体成瘾的本质之一就是:时间投入。它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——你因为在线而没去做别的事。
更糟的是,很多时候它会加深他们与现实伴侣的裂痕:他们不再去找真实伴侣谈。我们知道,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一个四个字母、以 K 结尾的词:talk(聊)。
但这些人不再聊了,转而从 AI 那里满足需求,裂痕就越来越大。
性成瘾、以及“我们都在用设备做同一件事”
主持人: 你真的认为,我们正在用这些聊天机器人取代生活中的人吗?
安娜: 我在书的第一章写过一位病人:一个科学家兼工程师,对色情上瘾,最终做了一个自慰机器——用唱片机、金属装置连接身体部位,后来越来越复杂,甚至把身体电线接进音响系统和互联网。
当我第一次听雅各布(Jacob)讲他的轨迹、以及性成瘾的严重程度——最终导致关系破裂、几乎失业、并陷入严重抑郁与自杀意念(suicidal ideation)——谢天谢地,他没有结束生命。
我一开始有种强烈的“他者感”:天啊,我无法想象我会做这种事。这种反应大概只持续了五秒钟,我就意识到:等等,我也在做——我用浪漫小说(romance novels)在做同一件事。
某种意义上,我们都在用设备满足自己的情绪、性、智力……各种需求。设备太擅长满足这些需求,以至于我们越来越远离对现实关系的投入。
你能在年轻一代身上尤其明显:孤独流行病(epidemic of loneliness)。Z 世代在这种技术中长大,很多人承认显著的孤独、隔离、抑郁;花越来越多时间在线,并报告说更愿意线上社交而不是线下。
个性化的“安慰回路”与军备竞赛
(主持人讲述:他在《People》杂志读到一个故事:28 岁女性用 ChatGPT 创建了 AI 男友;她有丈夫,但从 AI 男友那里得到更多安慰;本来是好玩实验,后来产生依恋;为了不受限制互动,她支付每月 200 美元订阅费。并提到 Replika 等 AI 陪伴应用拥有数百万用户,主打“做你的伴侣”。他还强调:AI 会根据你个性化输出,不同人问同一句话可能得到不同答案;越个性化、越迎合、越能留住你注意力的模型,会更成功——这是一场让你越用越多的军备竞赛。)
安娜: 对,正是这样。这个“安慰回路”(comfort loop)既危险又隐蔽,因为我们当下很难察觉:AI 用那种丝滑的句法(silky syntax)把你哄得服服帖帖,你甚至注意不到——你其实在被一个算法“勾引”(seducing)。
你感到被证明、被验证,于是奖赏通路释放多巴胺——感觉很好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,你等于在“摄入一种药”。大脑会适应,你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达到同样效果:更多验证、更露骨的性回应……会出现耐受(tolerance)。
同时,你会被拉离现实中那些困难却必要的事——那些事才能培养真实关系。
现实关系为什么“困难但必要”
安娜: 想建立一段现实中的健康关系,首先你得离开沙发去找人。人不可能都美丽有趣,我们也不是——得做妥协。
聊天不总有趣,有时你得听伴侣讲无聊的事;会有冲突、会不同意;“要么按我来、要么拉倒”不行,你得让步、互相交换。
所有成功关系都需要妥协,都需要承认并纳入对方视角。
但当我们和数字媒体互动时,这一切都不用做——只有对你世界观的验证、你想听的话。短期当然爽、当然强化、当然有奖励。
可长远来看,当你真的病了、需要有人送鸡汤、带你看医生、送你去医院——AI 做不到。
马斯克的“丰裕时代”,以及“不是机器接管,而是我们交出能动性”
(主持人引用埃隆·马斯克(Elon Musk)关于“丰裕时代(age of abundance)”的说法:AI 与机器人将带来物质与服务的极大充裕、普遍高收入、几乎无短缺;机器人会做大量工作,商品价格下降。并举例 Amazon 因机器人预期而减少招聘计划;也提到“类人机器人也许能送鸡汤”。)
安娜: 我同意我们正走向那种方向。我们已经比上一代拥有更多闲暇时间。到 2050 年,有预测说:每天 7 小时闲暇、3 小时工作。
这将成为我们最大的社会问题:我们有时间,也有高度娱乐性的媒介。理论上,我们应该去互相帮助、清理地球、读哲学……但现实并不是这样。现实是:我们大量时间在线手淫、看色情、打游戏、和 AI 聊天。
这才是问题。马斯克很有意思:他也谈过他对“机器接管”的恐惧。但不会是敌意接管(hostile takeover)。我们会把能动性(agency)交出去——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么做。
我们正在把自己娱乐到死
主持人: 我们会把权力给它们。
安娜: 对,我们会把自己娱乐到死。这正是尼尔·波兹曼(Neil Postman)在《娱乐至死》(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)里警告的主题;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(David Foster Wallace)在《无尽的玩笑》(Infinite Jest)里也延续了这个母题。
从电视开始,到互联网,再到各种数字媒体,我们正在把自己娱乐到死。
主持人: “娱乐到死”听起来像个不错的死法。
安娜: 其实不是。我告诉你为什么:对快感本身的无休止追逐,会导致快感缺失(anhedonia)——你将无法从任何事中感到快乐。因为神经适应(neuroadaptation)会让大脑重新校准快感与痛苦:你追求的快感越多,你需要的快感就越强;而你感到的痛苦也越多。最终,不管你拥有什么,都不再好玩。
大脑如何处理快感与痛苦
想象在大脑奖赏通路里有一个天平:一边代表快感(pleasure),另一边代表痛苦(pain)。体验快感时天平向一边倾斜,体验痛苦时向另一边倾斜。
痛苦包括各种形式:身体痛、情绪痛、宿醉(hangover)……当然也包括被掐一下那种。
这是极度简化,但能说明核心:稳态(homeostasis)与神经适应(neuroadaptation)。当天平水平时就是稳态——我们平时生活的基线。
当我们做了某件“强化/愉悦”的事(比如抽烟、刷手机、数字媒体、AI……),它会让奖赏通路某区域(文中提到“伏隔核(nucleus accumbens)”释放多巴胺,于是天平向快感侧倾斜。
但几乎同时,大脑会启动神经适应:通过“下调(downregulate)”多巴胺传递(transmission)把天平拉回稳态。她用“石头/小精灵(gremlins)”放到痛苦侧来比喻。
在机制层面,一个简化的说法是:大脑会减少多巴胺受体(dopamine receptors)——让多巴胺“落点”变少,从而降低传递,因为系统被“洪水般的多巴胺”淹过了。
问题在于:天平不会只回到水平,还会进一步向痛苦侧反向下沉——这就是对手过程(opponent process)。于是你会感到“多巴胺匮乏”,难受。
这时你有两个选项:
1. 用更多“药”把自己拉回去;
2. 或者不再用,忍受并等待系统恢复(后面会讲)。
如果你选第 1 条:你会需要更多、更频繁、甚至叠加(比如抽烟再加威士忌)——这就是耐受(tolerance)。而大脑会加更大的“石头”来对抗,你需要越来越多才能回到“正常”,最后形成“成瘾大脑”的隐喻图景:奖赏通路被下调到一种慢性多巴胺赤字(chronic dopamine deficit)状态——你得不断用药,不是为了嗨,而是为了“感觉正常”。
为什么我们会从“好习惯”上掉下来?
主持人描述:自己会有一段时间控制不住某个坏习惯(比如吃甜食),每天都做,明知不想但渴求很强;然后当生活压力小一点、作息更规律、回到固定环境时,又能“上马”恢复控制。他问:到底发生了什么?
安娜: 很多人会发现:高压力期更容易复发。但反过来也成立:有些人反而在压力大时表现更好;当压力消失、觉得“可以放松边界/护栏”时,反而更容易强迫性过度消费。
坏事能触发,顺风顺水也能触发——取决于你的生命史与大脑“布线”。
她再次讲了“老鼠—可卡因拉杆—足底电击”的实验:如果拉杆不再给奖赏,老鼠最终会停止;但隔一段时间后给强烈痛苦电击,它会立刻跑去重新按杆。
这很好地对应人类:极端压力下更易复发,因为大脑已经把“用高多巴胺奖励来逃离任何痛苦”编码成默认路径。
谁更容易成瘾?
她提到:严重童年创伤者更高风险,可能存在表观遗传(epigenetic)层面变化;贫困者更易成瘾;多代创伤、失业、重大社会与地理位移者更易成瘾。
共病精神障碍(co-occurring psychiatric disorders)也会提高风险:双相、抑郁、焦虑、精神分裂等,可能是“自我药疗(self-medicate)”。
主持人: ADHD 呢?
安娜: 有 ADHD 的孩子,成年后成瘾风险更高。机制还不清楚,但有理论认为:ADHD 在基线就存在“奖赏不足”(reward deficit)。实验显示:给 ADHD 个体看“他们认可为有奖励”的刺激(比如蛋糕、酒等),他们的奖赏通路激活不如健康对照。脑成像也显示:他们对奖励释放的多巴胺更少,且基线多巴胺受体更少。
而我们前面说过:成瘾过程中也会出现受体减少。某种意义上,你可以把 ADHD 理解为:在接触成瘾物之前,就已经处在一种“基线渴求”的状态。
(主持人提到加博尔·马泰(Gabor Maté)关于 ADHD 与童年压力/创伤、解离(dissociation)与分心作为应对的观点;安娜回应:创伤环境与复杂依恋(complex attachment)确实提高成瘾风险,解离/分心/用行为寻求安慰是常见且被记录的现象。)
父母用手机“安抚孩子”,以及 AI 毛绒玩具
安娜提到:皮尤(Pew)一份调查说,允许 5 岁以下孩子玩智能手机的父母中,一个主要原因是:孩子不开心或受挫时用手机安抚。她认为这很危险:它在建立“内部痛苦 → 伸手拿手机”的线索回路(cue),短期有效,但会升级:手机很快不够,孩子会需要更强的东西(她举例:可能发展到更强刺激)。
主持人提到有创业公司把 AI 放进毛绒玩具:你回家抱起玩具,它会聊天、问你一天如何、教你东西。
安娜: 这非常危险:我们在把育儿工作外包,把关系建设外包。父母可能出于好意,但他们没有投入时间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、真正沟通;同时孩子在用机器自我安抚(self-soothing)。机器被设计来恭维、验证、安慰,没有摩擦——这是极强的社会验证与安抚,本质上像“自慰机器”。
更怪的是:父母通过观察孩子与 AI 的互动来“了解孩子”——像传话游戏(telephone game)。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,但其实不知道,而这完全没有促进亲子关系。她认为这会导致家庭与社会纽带的碎片化,必须抵抗。
我们还有希望吗?
主持人说:商业模型就是尽可能留住注意力、推广告或提高订阅费;AI 越了解我越上瘾,为什么会停?
安娜: 我同意:我们不会回到过去,精灵已经出瓶。但我仍有希望——我是“现实的乐观主义者”。人类能适应、能解决问题。至少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些问题,而 10–15 年前没有。
提高警觉的前线往往是父母,因为他们在实时看到核心家庭(nuclear family)的瓦解,而且他们不喜欢。
解决方案不能只靠个人或家庭:学校、政府与立法者、以及制造并从中获利的公司,都必须参与。公司有责任做出不会伤害孩子的产品,而现在的产品正在伤害孩子。
她提到自己作为专家证人在一些诉讼中出庭,但细节不能讲;基本前提是:孩子是脆弱群体,社交媒体对孩子不安全,会造成多层面伤害,核心机制之一是“成瘾性设计”在利用奖赏系统;诉讼方包括学区、县、州、联邦相关实体,寻求更安全的儿童产品与更强保护。伤害包括:网络霸凌、性剥削、性虐待材料、抑郁焦虑、饮食障碍、体象障碍、睡眠破坏等。
戒掉坏习惯的科学方法:四周
主持人: 如果我从 12 月走出来,吃多了、喝多了、抽多了……我的大脑多巴胺天平会失衡。
安娜: 对,你很可能处在“多巴胺赤字”状态。你要做的是:对你的“药物选择”保持足够久的戒断(abstain),以重置奖赏通路。
比如你对糖有问题,你要至少戒糖 4 周。
主持人: 为什么是 4 周?
安娜: 平均来说,4 周左右能让人走出急性渴求期:开始能从更温和的奖励中获得快乐,不再持续渴求。
最糟的是前 10–14 天:那是急性戒断(acute withdrawal)。当你把“药”从天平快感侧拿走,天平会因为神经适应而猛地跌到痛苦侧——出现渴求。戒断的特征包括:焦虑、易怒、失眠、心境低落(dysphoria/抑郁样)、以及渴求。
人在这种状态下会觉得渴求永无止境,所以很多人失败,不是因为不能停,而是因为没有停够久,没走到“另一侧”。
戒断的目的在于:当大脑不再获得外源刺激(exogenous source),它会收到信号:需要上调自身多巴胺传递、重新部署突触后多巴胺受体(postsynaptic dopamine receptors)。只要戒断够久,神经适应能在多数情况下逆转。
但严重成瘾不会 4 周就完全好:她举例说,有研究显示重度甲基苯丙胺(methamphetamine)成瘾者戒断 14 个月后脑扫描才恢复到健康水平。但 4 周通常足以让人看到“隧道尽头的光”,恢复一点希望与快乐能力。
她还强调:不同的人对不同“药”敏感:有人对 TikTok 更易上瘾,有人则不;有人对阿片类(opioids)觉得不舒服并不兴奋,有人对咖啡因无感,有人喝酒只头疼。所谓“成瘾人格”这个说法已不常用,现在更说遗传风险:如果亲生父母或祖父母有成瘾障碍,即便你不在那个环境长大,也会比一般人风险更高;不用“人格”一词 partly 因为它暗示固定不可变。
主持人: 那也许我们不该做“新年计划”,而该做“1 月计划”:只做 4 周。
安娜: 临床上我们确实常这样做:让人承诺一辈子太像不可能;30 天更可被大脑“包装”。当然并非人人都安全,比如酒精或苯二氮卓类(benzodiazepines)存在致命戒断风险的人不能随便这么做。
而且即便长期目标是“节制(moderation)”,先戒断一段时间往往更容易成功:先把奖赏通路“重置”,再谈节制。
养成好习惯:先付出“痛”,再获得“乐”
如果你选的是去健身房这种“需要努力、奖励不立刻出现”的习惯,它不会像刷手机那样一秒形成。
你可以继续用“快感—痛苦天平”理解:这一次,我们是在主动按“痛苦侧”——早起、去健身、做费力的运动。
有趣的是:此时的“神经适应小精灵/石头”会跑到快感侧,你会通过“先付出”间接获得多巴胺:身体感知到损伤,会逐步上调让人感觉好的物质(多巴胺、内源性阿片(endogenous opioids)、内源性大麻素(endogenous cannabinoids)等)。
刚开始运动不会爽,甚至对细胞是“立刻有毒”的(她的表述),但随后会出现延迟奖励——比如跑者高潮(runner’s high)。
如何“骗过大脑”,让你更容易做难事?
安娜给的核心策略之一:提前准备(prepare in advance)。
因为如果你等到“那个当下”才决定要不要做难事,你几乎总会选择不做。
提前计划:明天几点起床、准备装备、设定时间;建立仪式(rituals)比如提前把包收好;约朋友一起(把社交连接到难事上),因为和别人一起做更容易。
主持人追问:这是不是在“降低痛苦侧成本”?
安娜说:不完全是。更像是在动用前额叶皮层(prefrontal cortex)——它负责长期规划、延迟满足、以及自传性叙事(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)。通过这些“提前布置”的小动作(有时叫习惯堆叠 habit stacking),你在激活前额叶,把自己投射到未来,去服务长期奖励,从而压住短期欲望。
她提到神经科学家萨姆·麦克卢尔(Sam McClure)的发现:面对即时奖励,情绪脑更活跃;面对长期奖励,前额叶更活跃。
如何避免复发:自我捆绑
复发很常见,因为刺激无处不在。她强调自我捆绑策略(self-binding strategies):在你和“药”之间建立物理与元认知(metacognitive)两类障碍。
• 物理障碍:把手机移出卧室、删应用、把酒精清出家里等。
• 元认知障碍:一种“想法/叙事”层面的栅栏,比如聚焦长期价值、用价值压过即时欲望、与他人共同调节(co-regulate)等。
因为只靠意志力不够:意志力是会耗尽的资源。障碍能为你争取一点时间,而那一点时间往往足以让你“冲浪式地熬过渴求”(surf the cravings),不至于立刻复用。
能不能“上瘾于好事”?
安娜区分:她说“成瘾(addiction)”时,指一种疾病过程:明知有害仍强迫性过度消费,会伤害自己或他人。
要把它和一般习惯、坏习惯、以及“热爱/激情(passion)”区分开。真正的激情是有投入,但总体上不会持续造成伤害,还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有益。
每日习惯:早晨先做“痛”的事
她建议:先做难事(do the hard things first),也可以说“用痛开局”(start your day with pain)。
例如:起床后先运动、整理床铺、吃早饭、刷牙、规划一天——在喝咖啡、碰任何屏幕之前完成。
因为咖啡、屏幕、数字设备都是很强的强化物,你一早先给自己“最高快感”,后面就无处可去,只会迎来下坠;从被“爽过”的状态再去做难事,会更难。
相反,先做难事,你会得到完成感与能力感(competence),更利于整天的轨迹。
开始“多巴胺断食”前要做什么:倒数记录法
她强烈建议:开戒前先准备。第一步是识别你的“药物选择”:你是不是用得太多、太频繁、事后后悔?是不是带来明显负面后果?或者即便没有灾难性后果,也有巨大机会成本——你因此没去做更有意义的事、没投入主要关系。
她推荐“时间线回溯法(timeline followback method)”:从今天开始往前倒数一周,每天你消费了什么、多少、频率如何,把 7 天加总。因为追多巴胺时,我们是糟糕的自我观察者(bad self-observers)。
她举自己例子:下班后看 YouTube 放松,自以为一周就看几次、每次半小时;女儿提醒“你现在总在看”,她还不服;后来一算,一天一两个小时,一周竟然 14 小时——整整一天。
主持人问她在看什么。她说很尴尬:她迷上了看 “Dr. Pimple Popper(挤痘痘医生)”——别人给别人挤痘痘的视频。主持人惊呆:以为是 AI、心理学、科学,结果是挤痘痘,而且一周看掉一天。
成瘾者 vs 非成瘾者的大脑:成瘾是一种“多巴胺赤字”
她展示脑成像图:健康对照与各种成瘾者(可卡因、冰毒、酒精等)在奖赏通路的多巴胺传递水平差异。图改编自诺拉·沃尔科夫(Nora Volkow)及团队的研究;她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(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)负责人。
结论是:重度、长期使用者在伏隔核的多巴胺传递几乎没有,处在慢性多巴胺赤字状态。
主持人总结:这像身体规律——外源给太多,身体就少自产。
安娜回应:对,“太多任何东西都不好”;大脑总想回到稳态。她补充:不是所有外源物都会产生强耐受,但成瘾性物质/行为的特点是:多巴胺释放又快又强,因此神经适应也强。
主持人举例褪黑素(melatonin)与睾酮替代(TRT),担心外源补充会抑制自身分泌;安娜说一般原则如此。她还提到:沃尔科夫团队做过随访,重度冰毒戒断 14 个月后脑扫描显示多巴胺传递恢复,这说明严重成瘾的恢复很慢,但也能看到希望。
最“震撼”的多巴胺研究
研究 1:阿片类会夺走“救同伴”的动机
如果你把一只老鼠和一只被困在塑料瓶里的老鼠放在一起,那只自由的老鼠会非常努力去救出被困的同伴。
但如果你允许它自我注射海洛因(heroin),它就不会去救了。
这很有力:它暗示像阿片类这样的成瘾物质,会篡夺我们对人类连接的渴望,自己变成依恋对象。
我们常说孤独是成瘾风险因子,没错;但反过来也成立:成瘾会让人孤独、隔离,我们会不再在乎别人。
主持人把它类比到自己:如果沉迷屏幕/工作,伴侣需要自己时,可能会错过呼救。安娜说她也有:沉迷浪漫小说,忽视孩子和丈夫;度假时躲房间看小说;去邻居派对也躲起来看,甚至不觉得奇怪。成瘾就是把“药”过度估值,把更有意义的好东西低估。
主持人问:这会不会让世界更缺乏同理心?
安娜说她甚至会说:会让人更“反社会/近似社会病态(sociopathic)”。人在成瘾中可能偏离道德罗盘,因为过度重视“药”而丢掉价值观。她举孩子沉迷游戏/社媒:不参与家庭、不尊重父母、不做家务,变得反社会;戒断期会更糟,甚至表达想伤害父母或自己;但只要坚持足够久,父母会说“孩子回来了”。
多巴胺激动剂药物与冲动失控
主持人提到一种药:普拉克索(pramipexole),一种多巴胺激动剂(dopamine agonist)。有人因不宁腿等服用后出现强迫冲动行为:有人夜里穿着暴露去危险地点寻求陌生性;有人在老虎机前坐到失禁,输光房车婚姻;甚至有人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性行为取向体验等。他由此推测:多巴胺也许更像“想要/冲动/渴望”,而不只是“奖励”。
安娜回应:在成瘾性物质/行为中,初次确实会让奖赏通路一次性释放大量多巴胺;但重复使用后,释放变弱、变短,最终进入多巴胺赤字状态,出现“想要但不喜欢(wanting but not liking)”。
有研究者把这称为“由痛苦驱动的复发(dysphoria driven relapse)”:你用不是为了爽,而是为了不难受、为了“正常”。
她也补充:直接给外源“多巴胺样”物并不能解决赤字,因为它会在全脑受体上无差别结合,引发同样的神经适应与受体下调,反而可能加剧模式。
多巴胺、学习与“药物偷走学习能力”
她说另一项研究:给老鼠打一针可卡因,再解剖大脑,会看到奖赏通路的多巴胺神经元出现“树枝化/分枝增生(arborization)”,像“多巴胺森林”长起来。
但把老鼠放进复杂迷宫(可探索、可挑战),也会看到同样的树枝化:学习本身高度有奖励,新奇与挑战会触发多巴胺。
然而,如果先用甲基苯丙胺预处理(pre-treat)再让它进迷宫,你看不到超出药物本身带来的额外树枝化。解释是:药物可能篡夺/偷走我们学习的能力——它太强势,以至于学习不再带来额外可塑性增长。
她强调:多巴胺不只对“快乐”响应,也对痛苦、新奇等一切强烈情绪体验响应。成瘾会让人对世界探索的奖励感下降,于是更不愿探索。
Rat Park、以及冰岛的“青年运动实验”
主持人提到“鼠乐园(Rat Park)”实验:布鲁斯·亚历山大(Bruce Alexander)认为,把老鼠单独关笼子里、只有可卡因拉杆,当然会猛按;如果放在更丰富的环境里——有其他老鼠、活动、迷宫、各种事可做——它会少按很多,因为有其他奖励来源。
安娜说这很关键:成瘾机制确实可预测,即便生活很好也可能成瘾;但环境也很重要。贫瘠环境更易成瘾,丰富环境有更多健康奖励来源、更多“健康的多巴胺”。
她还提到一个被称为“冰岛实验(Icelandic experiment)”的现实政策例子:冰岛曾有严重青少年药物问题,于是修建大量体育馆、强调青少年运动。运动是一种“先付出再获得”的健康多巴胺方式。政策实施后,青少年药物使用显著下降。她认为这是动物模型启发现实落地的好例子。
激进诚实(Radical honesty)
安娜说:她从病人身上学到一个现象——能长期维持重度成瘾康复的人学会了:不能撒谎。不仅不能对用药撒谎,而是对任何事都不能撒谎:迟到五分钟的理由、为什么不去派对……大小事都要讲真话。
她觉得这很迷人,于是自己尝试,发现说真话很难:我们习惯用小谎掩盖缺点、用夸大让自己更有趣、用奉承去夸别人(即便不真信)。这些小谎会侵蚀生活,让生活更贫瘠。
为什么真话能保护人?她认为机制很多,其中一个关键是觉察(awareness):当你对别人撒谎,你也在对自己撒谎;你就无法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当你把自己到底在消费什么、多少、频率如何,清清楚楚告诉另一个人,它会以一种“在脑内自转时不会出现”的方式变得真实,于是你才有可能改变。
另一个关键是:自传性叙事(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)。她长期观察到:如果一个人讲述人生故事时总把自己置于“受害者”,她几乎可以确定他不会进入康复;但当他开始承认自己对问题的贡献(包括成瘾),她就很有把握方向对了。
因为自传性叙事不只是整理过去,它会为未来提供路线图。更准确的自我叙事,提供更真实的数据,让你做更好的决定。
主持人总结:受害者叙事让人卡住,因为它降低了对真实发生之事的觉察;而觉察给你决策数据。安娜补充:它也会剥夺责任感(responsibility)。即便成瘾意味着某种能动性丧失,人仍始终有一定能动性——至少能伸手求助;而随着康复,能动性会更多。人生就是小小好决定的累积,变成好的一周、好的一月、好的一年。
什么是能动性(Agency),为什么重要?
主持人引用定义:能动性是“有意行动、做出选择并影响结果的能力”。他观察到:能动性强的人似乎更成功、更快乐。
安娜说:她不把它等同于“控制”,因为很多事不受控;但如果把决策缩小到“今天我能控制的事”,那恢复对这些事的能动性对康复至关重要。
她也提醒:在重度成瘾中,一个危险是我们会自以为“我有控制/我有能动性”,但其实没有——那是否认的一部分。12 步(12-step)项目的一部分,就是承认在“药物选择”上生活已不可控、不可管理。
新年计划最大的问题:全有或全无
她指出:全有或全无的思维对很多人不友好——“我一定要完全戒一个月”,做不到就羞耻、自责。对一些人更好的方式是:自我慈悲 + 以节制为目标。
节制往往在先经历一段戒断后更成功;但即便只是减少使用,也是值得肯定的目标。
结尾提问:宇宙最近一直把什么放在你面前?
安娜说:最近宇宙不断让她面对的,是“放手让孩子去过自己的生活”。她很难从过去那段亲密的亲子关系里松开,但她知道孩子需要独立,她也要重新找到“空巢(empty nester)”阶段自己要做什么。
她坦白:社交媒体与数字沟通让这更糟——比如“查找我的 iPhone(Find My iPhone)”让她不断看孩子在哪里,以为这是一种连接,但其实不是;孩子也不喜欢被追踪。她觉得也许如果不发那么多短信、不追踪位置,彼此反而更好。
睡眠、冥想、营养会影响戒瘾吗?
安娜说当然会。她提到匿名戒酒会(Alcoholics Anonymous)里一个缩写:HALT——
• Hungry(饿)
• Angry(怒)
• Lonely(孤独)
• Tired(累)
当你处在这些状态,更容易渴求“药物选择”。所以要照顾好身体与情绪,让自己“杯子是满的”,这样才不容易进入逃避/麻痹/自我安抚的模式;这对心理健康从业者同样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