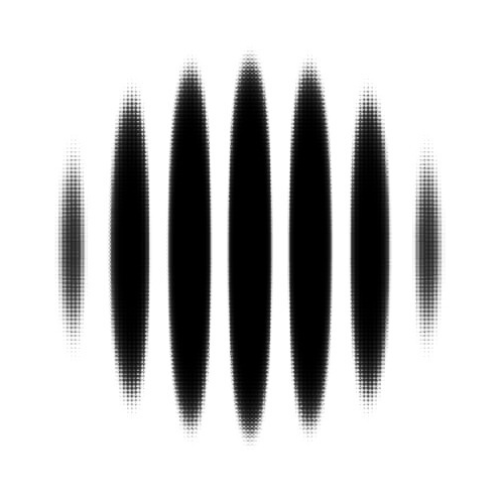设计,是一种爱的实践
Jony Ive 首次深度访谈:设计的尽头,是“你被在乎”的那一刻。

他是 Apple 的灵魂工匠,也是影响一代人审美的幕后推手。在这场与 Stripe 联合创始人 Patrick Collison 的长谈中,Jony Ive 首次深入讲述他对设计的信仰——不是风格、不是功能,而是爱与关怀的延伸。
他谈极简主义中的喜悦,谈团队文化的仪式感,谈创新的责任,也坦诚面对技术副作用的沉重。你将看到一个极致完美主义者,如何温柔地拆解设计的灵魂。
这是一次罕见的公开对谈——Stripe 联合创始人 Patrick Collison 邀请 Apple 前首席设计官 Jony Ive,共同探讨设计、创新与人的关系。发表于2025年5月9日。
Patrick Collison:我对这场对话非常兴奋。科技行业里,有些人几乎无需介绍,而 Johnny 就是其中之一。事实上,他甚至几乎不需要姓氏的加持。请大家欢迎——Sir Jony Ive。
Jony Ive:好吧,我们开始吧。非常感谢你的邀请。能在这里和 Patrick 一起交谈,我感到无比荣幸,真的非常感激。
Patrick:我想从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。虽然你可能没有机会亲自逛展区,但后台也有监视器可以看到一些情况。你觉得这次活动的设计怎么样?
Jony:很漂亮,不是吗?我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,但这里留给我一些非常强烈而清晰的回忆。设计确实很美。记得我第一次来旧金山参加的活动,就是你设计的,有只水獭在后面,应该是 WWDC,我要回头查一下,可能是 2005 或 2006 年。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旧金山的活动,好像就在这间 Moscone 会议厅。但那次是 John 能进主厅,我被安排到了溢出房间,真不是我的错(笑)。
Patrick:你是在 1992 年来到硅谷的,对吧?
Jony:对,那年我搬来了。虽然我现在还不算老(笑),但那确实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Patrick:Alan Kay 曾经说,软件和计算产业是一种“流行文化”,意思是我们没有历史感,也不了解那些塑造我们行业的思想和前因。这种现象挺有趣的,在很多行业里,开创者和先驱往往被视为殿堂级人物,可如果你问一些科技从业者“谁发明了互联网?”,很多人其实说不清楚。这让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你在这里观察了三十多年,你觉得硅谷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?
Jony:当年我还在艺术学院读书,主修的是设计。那时我在英国伦敦出生,后来到英国东北部念书。我记得直到最后一年才接触到 Mac——很遗憾没早点认识它。但那一刻,我意识到一件事:我们创造的事物,是我们是谁的见证;我们创造的东西,展现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关注点。这种领悟很有力量。看到 Mac 的时候,这种感觉特别强烈。
我感受到一群有着坚定价值观的原创思考者,他们显然非常关注人类和文化。你可以看得出来,有些产品是为了赶进度、满足成本目标而仓促打造的——这种产品事后总让人悔恨。但 Mac 给我的感觉完全相反,它是由一群加州的“异类”创造出来的,目的是推动人类的进步。这种理念让我非常震撼。
虽然我学的是工业设计,不是科技,但我被他们的信念、决心和勇气深深打动。我渴望认识这些人。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后的 1989 年,第一次来到美国。但因为当时拿了奖学金,所以必须先回伦敦履约。虽然听起来是小插曲,但这种状况反而给了我一种自由。如果我是为了找工作而来,我太害羞了,肯定没胆量去主动见人。但因为没有“目的性”,别人也不会防备我,自然更愿意见我。
Jony:所以,为了尽量回答你刚才的问题,我想说——我在 1989 年和 1992 年之间两次来到了这里。那时我开始为 Apple 做顾问,后来他们说服我正式搬来加州工作。
我所看到的,是一种带着天真色彩的狂喜——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共同的价值观聚集在一起,他们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服务。这种氛围在当时无论是小团队还是大公司之间,都很真实。我真的相信,那时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:我们在这里,是为了服务这个物种。
Patrick:那种感觉是在 Apple 里面,还是整个硅谷?
Jony:说实话,Patrick,我觉得那种氛围无处不在。即便大家是竞争对手,我也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信念:我们的位置是“服务者”,是有原则的服务。而现在……我不觉得这个信念还能完整地存在。
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尖锐,但今天有很多行为,是被金钱和权力驱动的。而这种变化往往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,而是一步步偏离轨道、逐渐走远的。
如果你把今天和 1992 年做一个清晰对比,我觉得这种判断还是合理的。
Patrick:那对于今天还在创造软件、打造产品、创业的人来说,他们该如何避免陷入这种偏离?在你看来,那个“北极星”是什么?应该坚持的核心是什么?
Jony:我认为必须有一套扎实的基础价值观,要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有清晰的认知。必须明确目标是什么:那就是激发和赋能人类。
你知道吗,Patrick 和我刚刚在后台聊到“工具制造者”这个身份。我非常清楚,也非常自豪,这是我的职业——我的实践。我热爱推动事物向前,也就是“创新”。
但我必须说一句,我很反感人们把“创新”误解为“要不一样”或者“要打破一切”。我完全没兴趣为了打破而打破。那种一味破坏、然后迅速前进的做法,最终只会带来一地狼藉。
我更感兴趣的是:如果我们打破了某些东西,是因为我们创造出了更好的东西。
人类总有一个误区,就是把进步当成必然发生的事。但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。你需要内在的信念,那是燃料。然后你还需要一个想法,一个愿景,再加上把愿景变为现实的决心。而且,这种愿景不应只属于我们自己,而应当能被广泛共享。
Patrick:你曾说过一句话,“sincerely elevate the species”(真诚地提升这个物种)。能谈谈这句话的背景吗?
Jony:当然,我记得很多次,尤其是周日下午,我在做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设计细节。比如包装,甚至是如何放电源线这种事。
听起来很荒谬吧?和你们在座各位做的事比起来,简直微不足道。但我非常清楚,有成百上千万的人会接触到这根小小的电源线。而我可以选择设计得让它更容易打开——听起来还是很琐碎对吧?但那一刻我意识到:如果一个用户打开盒子、拿出电源线的时候,感觉到“有人在乎我”——那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连接。
我觉得那是一种“灵性体验”。
Steve(乔布斯)也讲过类似的话,他的表达比我动人得多。他说,如果你用爱与关怀去创造某样东西,尽管你永远不会认识你的用户,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故事,他们也不会知道你的故事,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握手相见,但他们使用你创造的产品时,那就是一种传递感恩之情的方式。
他认为,这正是我们向这个物种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方式。
Patrick:当人们谈论你在 Apple 时期的设计,常会提到“极简主义”、“简洁”、“功能明确”这些词。这些当然都属实。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——很多设计里,其实蕴含着一种幽默感和喜悦感。
比如说像 Pixar 台灯那样的 iMac;比如五彩缤纷的“糖果”iMac;再比如甚至还有 iPod 的“袜子”。你怎么看“快乐”在设计中的角色?
Jony:这个问题太棒了。我觉得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:他们以为“简单”的产品,就是把杂乱无章的部分删掉。可那样做的结果,往往只是个不凌乱、但空洞无魂的产品。
一个“干瘪、毫无灵魂的产品”——你刚才那个说法太美了(笑)。很多现代主义或者极简主义的设计,最后就落到了这个境地。
而对我来说,“简洁”的目标是:用最凝练的方式表达出某个事物的本质,它的目的,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。
我一直觉得,在硅谷,甚至在整个科技行业中,“快乐”与“幽默”其实常常缺席。这点让我挺沉重的。
我们的产品本质上是很复杂的,对吧?而且“快乐”有时还会被误解成“轻浮”。
但我始终相信一件事——我在设计时的心境,最终会体现在作品之中。如果我内心充满焦虑,作品也会变得焦虑。
所以,保持一种希望感、乐观和喜悦的状态,不仅体现在我们彼此相处的方式上,也会最终体现在我们做出的产品中。
Patrick: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讲座,来自 Daniel Cook。他讲的是怎么构建一款“公主救援企业级应用”(Princess-saving enterprise application)。
他从经典的《超级马里奥》游戏出发,说马里奥的核心目标是“救出公主”。但他用企业级产品的设计视角重构了一遍过程,结果荒谬又有趣。
他抨击这种方法,说它忽视了一个事实:用户是“人”,是有学习能力的,会发生变化。而软件本身,是会对人产生影响的。
你刚才用的那些词——激发、赋能、爱、关怀、感恩、喜悦——在我看来,恰恰就是把“用户当作人”来看待的表达。
Jony:没错。我和 Patrick 曾经聊过一个现象,我想在这里尝试解释一下,希望你能帮我补充——因为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。
这是我在 Apple 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的事:当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,为同一个产品而努力时,会发生一种很奇特的现象。
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合群,要与人建立联系。工作中也是这样,希望大家多元共处、相互协作。
但我注意到一件事,曾经让我非常恼火,直到我换了一个更宽容的视角来理解它。
大家在讨论产品时,往往会围绕那些“可以量化的属性”去交流。
你们可以回忆一下,日常的产品会议里,讨论的常常是:进度表、成本、速度、重量——任何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东西。因为数字让人有共识,谁都知道 6 比 2 大。
我理解为什么会这样——这是人类试图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,是想要“更容易参与”。
但危险的事情来了。我把这称作“潜移默化的谎言”:
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那些容易量化的属性上,于是我们慢慢相信——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。
但这根本是谎言。
那些数字虽然重要,却只是“部分真相”。
而像我这样的设计师,或者其他创意工作者,能带来的真正价值,往往不容易量化。但这些体验、喜悦、使用的愉悦感,恰恰能让人更频繁、更深度地使用产品。
Patrick:我们刚谈到设计的影响与重要性。那我们稍微切换一下话题,聊聊设计的实践层面。
质量和速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取舍?也就是说,我们是不是必须在两者之间做选择?
Jony:有时候,确实存在这种权衡。
Patrick:我还以为你会说“不会”。
Jony:(笑)我当然希望能说“不会”,但现实是,有时候确实有取舍。不过我更倾向于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:它其实是关于“动机”。
当你陷入“只能二选一”的情境时,我会变得固执,会说“不,我不要选择,我要兼得”。
的确,要做到高质量、高速度、低成本,并不容易。
但我相信,在效率中也存在美感。所以我们说的“速度”,我更愿意称为“优雅高效地工作”。
我知道你我都非常在意我们使用的语言,因为语言塑造思维,定义问题的方式往往决定了解法。
所以对我来说,这个问题应当被表述为:“我们如何以极致高效的方式,去打造出令人惊叹的品质”。
Patrick:那当组织开始扩大,情况又变得更复杂了。
在最初期,也许你只有自己一个人,然后可能再加一个两个人,大家什么事都清楚,什么决定都能亲自把关,所有细节你都能亲手参与。
但随着规模扩大,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:有些决策你没看到,有些产品部分你没机会参与。你甚至会说:“我不知道他们为啥要那样做,我肯定不会那样做”。
在 Apple 后期,你面对的正是一个庞大的组织。你是怎么处理这类“距离感”的?尤其是当一个结果“不合你口味”的时候。
Jony:我认为,说“这不是我喜欢的方式”,完全合理,非常合理。
但确实——这非常困难。
我相信,我们会在人生和事业中经历一个个“章节”。最痛苦的是从一个章节走向下一个——你需要调整,改变做事的方式。
最关键的一点是:不要以为你是怎么开始的,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。
所以,明确你绝对不愿妥协的是什么,那些“原则、价值观、动机”——这非常重要。
我每次感到警觉,往往是当我回头想: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?我这样做,是不是出于原来的动机?”如果不是,我会对自己失望,然后重新校准。
但我确实相信,如果我们的动机和价值观始终如一,我们总能找到办法,继续成为那个天生的“控制狂”——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“对细节极度在乎的人”,不过,说实话,还是“控制狂”更真实(笑)。
Patrick:对于你所带领或参与的设计团队来说,有没有一些特别的“仪式”?
Jony:有的。对我来说,没有什么比“创意团队”更重要的了。这一点,我始终非常清楚,也会反复表达:这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所能贡献的核心。
不过,这只是“入场券”。
你可以招到厉害的人,但光有天才不够——我们的“实践方式”、“工作流程”、“行为准则”才是关键。
我带设计团队三十多年了,积累了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。
因为我们经常处理的是不能量化的概念,是那些从“念头”到“讨论”到“原型”逐渐演变的想法。而这些初始阶段的创意往往是非常脆弱、非常容易破碎的。
这时候,“小团队”“相互信任”“彼此关心”变得至关重要。
如果你真心在乎别人,那你就可能有耐心去“聆听”。而我发现,在很多地方,点子之所以夭折,是因为大家太渴望表达、太想抢话了。
很多好点子,是被“发言欲”淹没的。
我们必须清楚一点:“意见”和“创意”不是一回事。
我本来想说句很毒舌的话(笑),但我忍住了。
保持安静,去倾听——这是我特别在意的事。因为我知道,在我职业生涯中,有些精彩的想法来自“安静的人”,而我却可能因为没能听到它们而错过。这种遗憾让我非常害怕。
所以谈到“团队仪式”,我发现最有效的一种方式,是:为彼此创造点什么。
这是一种每天都可以进行的连接方式。思考“我能为团队的伙伴做点什么”,哪怕是微小的事。
这会让你把注意力从“我”转移到“他人”,让你愿意变得更脆弱,也让对方感到被珍惜。
就这几点——“在意他人”“愿意脆弱”“心怀感激”——如果你细想,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很美好的文化雏形。
Patrick:Paul Graham 说:“做出人们想要的东西。”而你则说:“为彼此做点东西。”
Jony:对呀,这就是我们做的事,不是吗?
我们所有人,其实都是在个人层面上,实践着我们在专业层面的工作——为他人而做。
我不太确定“做出人们想要的东西”算不算是一种商业策略,而我说的“为彼此做”,更像是一种团队策略。
Patrick:你说得很好。比如说你们团队有一个传统——每周五早上,轮流由一个人给大家做早餐。
我本来以为你说的“为彼此做点东西”,是指“原型 iPhone”之类,结果是“培根蛋饼”啊(笑)!
Jony:(笑)我们有的就是麦片加牛奶。有时候早餐水准很高,有时候非常惨不忍睹。但无论好坏,它们背后的动机都一样。
还有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“仪式”,也是我们在 Apple 尝试的实验之一,结果意外地特别有力量——那就是我们轮流邀请团队成员到自己家中工作一天。
这个点我可能想得太多了(笑),但它真的带来了很多好处。
首先,它促使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做出更好的作品;其次,它也塑造了团队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。
当你邀请大家来你家工作时,会不自觉地紧张,担心他们会不会对你的沙发套品头论足(笑)。就像你请人来家里做客一样,会有一种不安和自我意识。
而作为“客人”的同事们,他们也会表现得更礼貌、更得体——这和走进公司会议室是完全不同的状态。
然后就是“环境”本身的影响:如果你是在别人的客厅里,坐在沙发上,或是盘腿坐在地毯上,手边是你的笔记本和草图本——你脑子里想的问题,和你在那种冷冰冰的会议室里,是截然不同的。
Patrick:美是主观的,还是客观的?
(停顿,笑)看来我们终于来到简单问题了。
Jony:哈哈。我觉得……可能是两者兼具。
我认为,如果一个东西不能用,那它就是丑的。
我一直以来都很反感人们试图把“实用性”和“美感”对立起来。当我参与设计的某个东西不能正常工作时,不管它长得多漂亮,我都认为它是丑的。
真正难的是当我们谈论“品味”的时候。
设计一直都是一个很微妙的领域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可问题是:每一个人的意见,并不都等值。
我想,这个说法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——如果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设计,你的判断力是会有所提升的。虽然我也认识一些学了很多设计、但品味仍旧糟糕的人(笑)。
所以……嗯,是个好问题。
Patrick:Christopher Alexander 曾说过,当你在两个选项、两个方向之间犹豫时,选那个“更有人性”的路径,因为“人性”的感受,比单纯的“美感”更值得依赖。
你觉得他说得对吗,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?
Jony:不,我完全认同。他说得非常对。
我认为,大多数公司都在“低估”用户——在“施舍式”地对待用户。我始终相信用户其实是非常敏锐的、极具感知力的。
所谓“美”、“人性”,其实都和这种感知能力相关。
这也回到了我们最初讨论的那个点——我第一次看到 Mac 的时候,我能感受到它背后的团队充满了关怀。我一直试图表达这件事,虽然我很希望自己能有更扎实的实证依据,但我真的相信,我们能感受到关怀。
在面对面服务里,这很容易理解:你直接接触到服务者的态度,你能感受到“你是否被在乎”。
可如果是透过一件物品,或是一个软件呢?这种“间接的关怀”会变得更复杂。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。
如果你还不确信,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:你一定能感受到“漠视”吧?
我们很容易察觉“草率”、“敷衍”的态度——那反过来,我们也一定有能力察觉“爱”与“用心”。
在 Apple,我们会花很多心思去“打磨产品内部”,哪怕那些地方用户看不到。
就像优秀的木匠会认真打磨抽屉背面——即便没人看得见。
这并不只是工艺上的坚持,而是一种态度:你在无人注视时做的事情,才真正代表你是谁。
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“进化程度”的体现。只注重表面,是肤浅的;而如果你对细节、对内部同样关心,那就是一种深层的美德。
如果我们只做表面,我会一直有种隐隐作痛的感觉——我们只是在“摆样子”。
Patrick:你之前提到“现代主义”,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早期现代主义,常常是故意“不美”的——比如杜尚的《泉》;甚至像毕加索的很多作品,也都带有不和谐感,它们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“美”。
那时候,很多设计理念带着政治色彩。Gropius 就说包豪斯是一场“社会主义运动”。
而你也曾受过包豪斯体系的训练,对吧?
Jony:对,是的。
Patrick:Apple 的设计风格是极致简约的,非常漂亮。但 Apple 显然不是一家社会主义公司。
所以这让我有些困惑:早期现代主义似乎在刻意追求不和谐、打破传统美感,甚至带有某种“震撼性”;而你在 Apple 做的设计却追求极致之美。
所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?你现在离开 Apple 也几年了,回过头来看,你怎么看“现代主义”这个东西?
Jony:这问题很棒。
我觉得,往往一个设计运动刚刚起步时,会带有一种“能量爆发”的状态。它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的宣言。
在那样的阶段,“美”可能不是最先考虑的东西。美,往往需要时间去酝酿、去打磨。
而最初的那股原始能量,是迅猛的、野性的,不会有太多时间去顾及“和谐”或“优雅”。
尤其在艺术领域,很多艺术家会主动回避“美感”这种传统概念——他们不想被它限制,或者干脆认为美感是一种干扰。
举个例子:很多现代主义作品之所以长那个样子,是因为他们对某种“新材料”充满了迷恋。
你说到包豪斯,那是一个诞生于德国的伟大运动,横跨美术、家具、建筑……你们可能最熟悉的是那种“钢管椅”。
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抛光过的、弯曲的金属管——他们刚刚学会怎么把金属管弯出曲线,而且不让它折断。
你知道吗?他们是通过在金属管里塞弹簧,才实现了弯曲时不塌陷的。
所以他们就开始拼命地“弯管子”!这也不奇怪——如果我刚学会这个技术,我也会拼命用它(笑)。
那时候,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“美”,而是材料的可能性,是工艺的突破。
Patrick:现在看你们 LoveFrom 的一些作品,包括你们最近参与的几个大型项目,我感觉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——我私下称之为“Johnny 的装饰时期”。
因为 Apple 的设计是极致简洁的,而你最近的作品则开始探索更多风格、甚至更多“装饰性”。
这是我的错觉,还是你真的在尝试一种风格上的解放?
Jony:哈哈,我觉得你的观察很到位。
我离开 Apple 已经快六年了。当时的目标,是组建一个“最非凡的创意团队”。现在我们有大概五六十人,很多设计师是我在 Apple 共事多年的老搭档。
但我们现在的团队非常多元——有工业设计师、平面设计师、界面设计师、建筑师、字体设计师、音乐人、声音设计师……
所以你看到的变化,其实也是我们合作对象的多样化导致的。
以前,我们服务的是 Apple,目标明确,标准清晰。
但现在,比如我们为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设计视觉系统——那当然和为 iMac 用户设计说明书完全不同,所需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不同。
所以,我现在更关注的是:“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”
Patrick:你一直在谈设计的意义,以及它对使用者的影响。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:今天关于智能手机、互联网的影响,尤其是对注意力、对青少年的影响,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讨论。
这些产品并不都是你主导的,但它们中的一部分你参与得很深。人们也在担心 AI 会不会影响教育、作弊、学习方式,甚至整个心智结构。
所以想问你,作为一个始终严肃看待“作品影响”的设计师,你是如何思考这些“潜在危害”的?
Jony:你问的这个问题,大概是目前让我最困扰、也最牵挂的议题。
在创新过程中,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料之外的后果。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后果大多是“愉快的惊喜”,但有时候,也会产生一些令人遗憾的负面影响。
我个人参与过的一些产品,就确实带来了一些我未曾预料、也不那么正面的后果。
问题是,即使“初衷无害”,我们仍然有责任面对这些结果。我对此感到非常沉重。
特别棘手的是,我们现在所处的技术浪潮,来得太快了。
你回顾过去,比如工业革命时期,人类也经历过巨大的技术跃迁。但那个时候,社会是有时间停下来思考、建立结构、制定规则的。
我们讨论过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基础设施建筑——“抽水泵站”。
你想象一下,在那之前,人类历史上,城市的污水是直接流在街上的。而抽水泵的出现,第一次让污水悄无声息、持续可靠地从街道中消失。
而那些负责抽水的机械设备,被安放在宛如大教堂般的建筑里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宣示。
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:每当有重大技术变革发生时,社会就会受到冲击。而我们之所以能适应,是因为我们有时间建立起新的秩序、新的社会结构。
而现在,速度成了最大的风险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思,它就已经改变我们了。
不过,有一点让我觉得值得欣慰——现在每次有人谈论 AI,总会同时提到“安全”这个议题。
而对比之下,早些年我们谈论社交媒体时,几乎没有人提“安全”或“后果”。而我对社交媒体的破坏性,是非常非常担心的。
最令人警惕的,是那些连讨论都没人提起的问题。
所以是的,我确实认为我们前进得太快了。即便我们本无恶意,但如果我们所参与的某些技术,带来了伤害,那我们就必须正视并承担起责任。
这种责任感,也推动了我最近在从事的一些项目——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公开谈论,但我非常期待未来可以分享它们。
Patrick:你刚提到维多利亚泵站——本来我没打算问的,但既然你提了,那我想问一个结尾式的问题:
在你看来,人类历史上哪个时代、哪个地点,拥有“最好的设计”?
Jony:这真是一个好问题,我不敢轻易断言。但我必须说,我最近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设计简直着迷。
我和我们 LoveFrom 的团队,一直在研究那个时期。不只是物品本身,也包括它们带来的社会后果。
我很幸运能和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 Jamaima 合作,她今天好像也来了。她做了大量研究,包括实物、历史档案,也包括那段时期的社会变迁。
因为在我眼中,设计远不只是物件——它包括制度、文化、城市、家庭,甚至政治。
比如,英国在工业革命后期,有两家公司我非常钦佩:Cadbury 和 Fry’s。
这两家公司其实是由贵格会信仰者创立的,他们不仅制造产品,还设计员工住宅。
而且不是简陋的宿舍,而是完整的社区,有花园、有道路、有教堂——他们有一种对“城市”的责任感。
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个面向:第一次,大量人从乡村迁往城市,这在整个人类史上都是第一次。
他们意识到:“我们不是在造房子,我们在建社会。”
这些案例让我非常鼓舞。
类似的事情,也发生在美国,比如 Hershey(好时)公司在费城附近建立的员工社区。虽然我对那个案例了解不如前面两个深入,但精神是一致的。
所以我最喜欢的设计,是那种既有文化、又有政治、甚至有灵性,同时在城市和建筑中被体现出来的设计。
Patrick:你其实很少公开讲话,今天愿意来,真的让人非常感激。
我们现在所处的,是一个可编程的金融基础设施大会。但这里的企业来自各行各业、各个角落。
我想代替很多企业提一个问题:对于一家像 Stripe 这样的基础设施公司——或者说任何一个不是以“消费者界面”为主的公司——为什么还需要如此重视设计?
Jony:如果 Stripe 不重视设计,那它就不会是 Stripe,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。
我打心底相信:如果我们想以“一个人的身份”参与到这个物种的未来中去,我们根本就别无选择。
关心他人,是我们的义务,更是我们的特权。
佛洛伊德说过:“人的一生只有两件事:爱与工作(Work and Love)”。
既然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,那如果这份工作中,我们选择不去关心他人——那我们不仅是在让别人受苦,我们自己也会因此变得麻木和腐蚀。
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“选项”,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。而且是一种非常值得感恩的责任。
如果工作,是我表达关怀的方式,那我非常荣幸。
我不会把生活切割成“这是商业,这是个人”。我就是 Jony,就是这样活着的。
Patrick:我们都感受到你的真诚。今天的分享太珍贵了,感谢你,Jony。
Jony:谢谢你,Patri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