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多书,却记不住、讲不出?
Why books don’t work|By Andy Matuscha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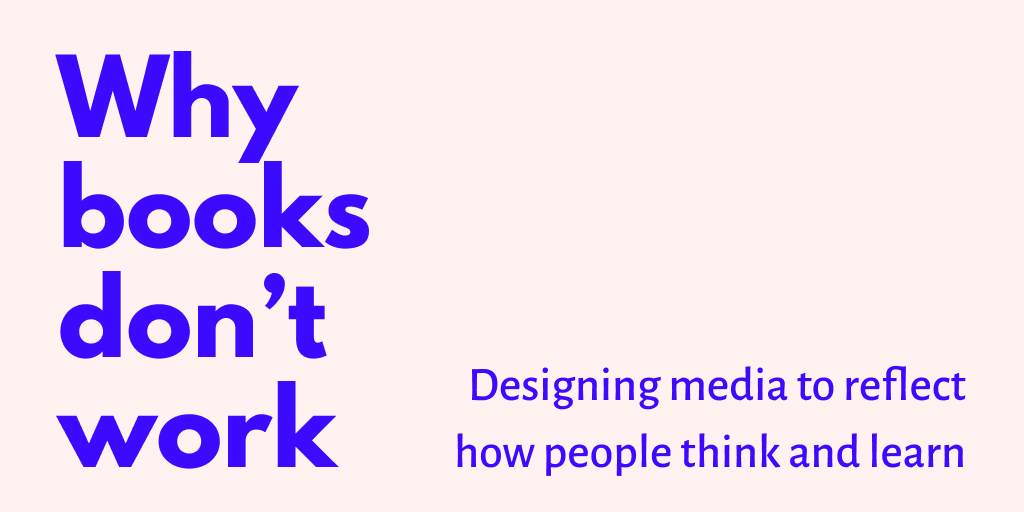
Andy Matuschak 是一位独立研究者,致力于打造能主动帮助人们理解、记忆和运用知识的全新阅读工具。他相信,计算机不仅可以传递信息,更能扩展我们的思维边界,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认知与创造力。
他曾参与 iOS 的开发,也曾在可汗学院领导研发,如今通过 Patreon 社区众筹推进前沿研究,是“思维工具”领域最具前瞻性的实践者之一。
书这种东西,实在太容易被我们理所当然了。我说的不是某本特定的书,而是“书”这种媒介形式:纸的也好,电子的也罢,通通是段落、页码、章节组成的那一类。尤其在非虚构写作中,书籍有一个几乎不被质疑的基本假设:人们是通过阅读句子来吸收知识的。这个观念早已深入人心,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——可惜的是,正如你将看到的,这个观念其实大错特错。
想象几本经典的严肃非虚构作品,比如《自私的基因》《思考,快与慢》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…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:读完一本这样的书,后来在某次谈话中提到它,结果发现自己真正吸收的内容,可能就只有寥寥几句话?我得坦白说,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一开始聊得还不错,能把书的大意讲个七七八八,但别人只要稍微往深处问一个问题,整个认知立刻土崩瓦解。有时候是记忆问题,根本想不起来细节;但更多时候,我惊觉自己其实从没真正搞懂书中的那个观点——尽管当时读的时候自以为懂了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,原来我几乎什么都没真正吸收。
我知道我不是个例。我和很多重视学习的朋友聊过这件事,几乎每个人都点头如捣蒜。这样的谈话往往像忏悔:大家有点不好意思,仿佛这是某种个人缺陷。我不认为这是缺陷——但无论是什么,它绝对不是少数现象。只是因为我们很难察觉这其实是“常态”,才会觉得尴尬。
我们说的这些书,可都不是小打小闹。每本动辄需要 6 到 9 小时来读。美国成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每天阅读 24 分钟,那一本书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啃完。这些书动辄卖出几百万本,总计花费的时间就是几千万小时。那么——作者想传达的知识,真的被大多数读者吸收了吗?哪怕只是读者自己原本期望获得的那部分?我的直觉是,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,可能是极少数。可惜我没找到相关的正式研究,只能诉诸你的直觉。
当然,我不是说这些时间都白费了。很多读者享受阅读过程,这很好。大多数人确实也吸收了一些东西,哪怕模糊难言:比如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、某种思维习惯、价值观、灵感等等。对于很多书(尤其是小说)来说,这些模糊的东西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意义。
但本文谈的不是这类书。我们讨论的是解释型非虚构作品,那些试图传递具体、细致知识的书。也许有人读《思考,快与慢》只是为了打发时间,但如果我们花了几千万小时去读,大多数人显然是希望能真正学到点什么。不然我们也不会在发现自己其实没吸收什么时感到震惊了。
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有点离谱的结论:作为一种媒介,书籍在传递知识方面意外地低效,而读者往往毫无察觉。
这个结论之所以离谱,一部分原因是:书确实也可以非常强大。在纪录片《宇宙》中,卡尔·萨根曾用一段话礼赞书籍:
“书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东西——它是一块从树上造出来的扁平物体,上面印满了奇怪的黑色符号。可只需看上一眼,你就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大脑,或许是某个几千年前已经去世的人。作者横跨千年时空,在你脑海里清晰而无声地向你述说。写作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,它把素未谋面的人连接在一起,把不同时代的公民联系起来。书打破了时间的枷锁,是人类拥有魔法的证明。”
没错,书是神奇的发明!在大众传播时代,它们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,也确实让一部分人真正吸收了深刻的知识。那么,为什么书有时候有效,有时候却不行?这个媒介,为什么会失灵?
本文接下来会试着解答这些问题:为什么书这么常常“失效”?又在什么情况下,它们又能“成功”?
先说明一下:我完全知道这篇文章本身就是“用书写的方式在批评书写方式”——但如果本文提出的想法能真正起作用,未来有关这个话题的表达方式,就未必还需要文字了。这篇文章,姑且当作点燃篝火的引子吧。它若最终被火焰吞噬,我会感到无比欣慰。
当我们理解了书为何失灵,或许就能找到改进它的方法——甚至大胆设想一种全新媒介,不是用纸,也不是用像素,而是用人类认知本身为材料,重新织就。
为什么讲座也没那么管用
刚才我们讲的是书,但你是否也在听讲座时,遇到过类似的体验?听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听懂了,结果一到晚上做作业,才发现其实根本没掌握多少内容。你可能会归咎于记忆力,觉得“我记得我当时懂的,只是后来忘了”。可事情往往不止是记忆问题——当你试着回想讲座的内容,常常会发现:你当时根本就没真正弄懂,只是误以为自己懂了。
相比起书籍的“失效”,人们对讲座不管用的现象其实更能接受。毕竟,这样的教学片段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?
“约翰逊老师每天在讲台上讲满一小时,以为学生都听懂了——然后他开始纳闷为什么大家考试分数这么低。”
像书一样,讲座也可以是愉悦的、启发性的;也像书一样,讲座有时候确实是有效的,对某些人来说。但你大概不会真的认为,讲座是一种可靠的知识传递方式。
问题的根源在于:讲座和书籍有着相同的失败机制。这两种媒介都没有建立在“人是如何真正学习的”这个问题之上。它们是在缺乏学习理论指导的情况下,在错误的前提下自发演化出来的。
举个例子:你可能已经总结出一些对你有帮助的学习方式,比如解题、写总结、做项目等等。这些方法并不是魔法,它们之所以有效,是因为它们契合了你认知系统的某些规律。更准确地说,它们反映了人类普遍的学习机制。
如果我们能收集到足够多这类“认知底层规律”,就能总结出一些关于学习如何发生的认知模型(cognitive models)。不同的学习方法可能背后指向同一个模型,也可能互相冲突。有些模型可以被实证检验,有些不能,还有些已经被证伪。通过研究这些模型,而不是零散的技巧,我们才能找到更普遍、更系统的启示。比如:如果我们相信某个认知模型成立,那它意味着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有效,哪些无效?
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,因为——知识传递是一件非常难的事。大多数听讲座的人没能真正学到讲者想教的内容;大多数读书的人也没有真正吸收到作者想传递的知识。失败,是默认状态。所以,如果你想让别人真正理解你的观点,那你最好有一套清晰的认知策略支持你。你可能希望“把观点解释清楚就够了”,但现实是:复杂的概念,几乎从不会靠“讲清楚”就能被理解。
讲座之所以不行,是因为它这个媒介压根就没有建立在有效的认知模型上。如果你是个外星人,在地球上观察人类的讲座场景,你大概会以为他们默认的学习模型是这样的:
“老师讲一堆描述某个概念的词语;学生听了并做了一些笔记;学生就理解了。”
在教育心理学里,我们把这个模型叫作“传输主义”(transmissionism)。它假设知识可以像文字抄写那样,从一个人“直接传送”到另一个人脑子里。可惜,并没有这种好事。这个模型早就被否定了,现在在学界基本只用作贬义,专门用来批评那些“落后、天真的教学方法”。
当然,大部分优秀的讲师并不会真的相信“说一说大家就懂了”。但问题是:讲座这个形式本身,就像是默认了这种荒谬的模型,于是讲者往往也就不自觉地按照这个假设去设计和传递内容。
如果你去问讲师,他们很多人会给出一个稍微靠谱的解释:理解其实是在课后发生的,当学生在做习题、写论文时才真正消化了知识。讲座只是提供原材料。好吧,这个说法在认知科学里是有一定依据的。
但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这个模型,我们还会选择“现场、连续九十分钟的演讲”作为信息传递方式吗?
听众的注意力几分钟就开始漂移了,那我们是不是该把讲座和练习交叉穿插?
现场演讲无法暂停和重播,那这种方式是不是太容易丢信息了?
读文字的速度远比听人说话快,那我们是不是干脆用文字会更高效?
答案不言而喻:传统讲座的设计,并没有真正围绕认知模型展开。
“讲座只是热身,真正学习靠课后”——这个说法其实更像事后的自我安慰。但它确实触及了一个深刻的认知原则:理解,必须靠主动参与。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原则,课堂的形态将会彻底改变——互动讨论、实践项目将成为主角,而讲授只是为了服务这些活动。
这并不是空想:过去几十年,美国 K-12 教育政策的主旋律之一,正是围绕“摒弃讲授、倡导主动学习”展开的。
总结一下:讲座之所以不管用,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假设上——传输主义:老师说一说,学生听一听,就懂了。现实中,讲座如果偶尔有效,那也是因为它被包裹在一个更完整的学习体系中(比如项目制、问题驱动),这些体系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部分。讲座本身,并没有那么大的贡献。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认知科学的启示,恐怕讲座早就该被淘汰了——而这也确实正在发生。
而理解了讲座的问题,我们就更容易明白:书籍作为媒介,其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为什么书也没那么管用(再说一遍)
在讲座这个案例中,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直觉:一种媒介如果没有建立在真实的学习机制上,就很难真正传递知识。现在,我们把这个视角带回书籍,很快就会发现,书——作为一种媒介——其实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。
和讲座一样,书籍也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认知模型作为基础。但它们隐含着一个默认模型,而且这个模型和讲座一样,叫作传输主义(transmissionism)。
书是由一行行的句子组成,一页页排布,章节连接成册。这种形式暗示着:人们通过阅读句子来吸收知识。用最简化的方式描述这个模型:
“作者在书页上用语言描述一个观点;读者读这些语言;然后读者就理解了这个观点。当他们翻到最后一页,他们就‘完成’了这本书。”
当然,大多数作者并不真这么想。但问题是:这种假设隐藏得太深,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去质疑它。
有些作者若你追问他们,也许会给出一个更靠谱的认知模型:读者不能只是阅读文字,他们必须真正去思考。也许要做些笔记、跟别人讨论,甚至写篇回应文章。换句话说,书只是一个“热身”,真正的学习发生在后面。这个模型比传输主义合理多了,那我们来看看它在现实中是怎么体现的。
我们之前已经承认,有些人确实能从书中学到东西。关键在于,这些人确实在认真思考。他们阅读时的内心独白可能是:
- “这个观点让我想起了……”
- “这点和我以前理解的似乎有冲突……”
- “我不太明白它是怎么推导出来的……”
如果他们做笔记,也不是简单抄写原文,而是主动总结、提炼、分析。
问题来了:这些技能并不容易获得。读者必须掌握具体的“反思型阅读策略”:
- 我应该问自己什么问题?
- 我该如何总结刚读过的内容?
- 我到底有没有读懂?要不要重读?要不要查阅别的资料?
读者还必须理解自己的认知机制:
- “理解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感觉?”
- “我的盲点在哪儿?”
这一整套技能,学习科学有个专门术语:元认知(metacognition)。研究显示,元认知的学习难度很高,许多成年人都不具备这些能力【Baker, 1989】。更糟糕的是,即使有人掌握了这些技巧,实际运用时也非常耗神——特别当阅读内容是陌生领域时,这种“同时处理信息+自我调控”的任务变得更难【Langer & Nicolich, 1981;Baker & Brown, 1984】。
书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?如果我们相信“真正的理解来自于读者的深度思考”,那书籍到底做了哪些帮助呢?
一些优秀的作者确实在尽力。他们会构建读者的心理模型,预测可能出现的误解,并通过写作策略主动化解。他们也会有意识地控制内容的深浅,提示需要哪些背景知识。
这些努力确实能减轻部分元认知负担。但问题是,元认知是一个动态过程,它会随着读者的理解不断变化。而书是静态的:它能激发思考,却不能对你的思考做出任何回应。最终,读者还是要靠自己去规划反馈机制。
相比之下,讲座虽然也问题重重,但至少讲师还能设计作业、提供反馈。而书的作者——即便也认为“理解需要主动思考”——基本上是把所有的“思维练习”都交给了读者自己,没有反馈、没有引导。这种“边读边自我反思”的任务消耗极大,很可能还没来得及深入理解内容,就已经被“怎么思考”这件事搞得精疲力尽了。
(严格来说,这种“自己设计练习、自己检查反馈”的过程,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学习策略。但学习科学认为,它只对那些已经掌握相关内容和元认知技能的人有效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这种方法反而会降低理解效果【Kalyuga, 2009】。)
那如果我们真的以“帮助人思考”为目标来设计书籍,它们该长成什么样?
教科书是解决方案吗?
或许你会说:“那不就是教科书在做的事吗?我们只需要把《自私的基因》变成教材,插入练习题和讨论问题不就行了?”
确实,和普通非虚构书不同,教科书通常会明确构建自己的认知模型。它们会在讲解之后加练习题,引导学生以特定方式思考。光是这一点就比传统书籍进了一大步——但还远远不够。
为什么?很简单:大多数人依然很难靠教科书真正学懂。
首先我们观察一个现象:明明很多教科书都可以单独买来读,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报课程——花更多时间和金钱去上课。也就是说,教科书本身不足以让人安心“自学”,学生普遍觉得:跟着老师上课学效果更好。
为什么会这样?
回忆我们刚才说的:非虚构书让读者独自承担所有元认知任务,而教科书虽然增加了一些支持,比如练习题和小测验,但仍然让读者承担绝大多数的“思考设计”和“反馈调整”。
- 哪些题该做?什么时候做?
- 做对了,是不是代表我真的理解了?
- 做错了,该怎么办?去哪里查资料?
很多时候,练习题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出答案,而是为了揭示更深层的概念。可问题是:读者未必能意识到自己“虽然答对了,但没领会重点”。
这时,如果你有课程,情况就不一样了:
- 课程的教学计划帮你安排了节奏(你不用自己规划)
- 老师会给你反馈、讲评练习题
- 不懂的时候可以去上 office hour 问问题
- 同学之间可以讨论、澄清观点
- 甚至老师的语气和热情,都可能成为推动你深入学习的关键动力
也就是说,课程不仅分担了元认知压力,更提供了社会性、情绪性、动机性的支持——这些在教科书中几乎完全缺失。
在线教育和AI教学系统的确在尝试“复刻”这种功能,比如智能反馈、自动规划学习路径等。它们确实比传统教科书强,但依然过于聚焦于“任务执行”的层面,而忽视了学习中那些更深的、软性的成分——比如:
- 社会互动带来的启发
- 与教师产生连接所激发的热情
- 情绪唤起带来的记忆强化
- 环境结构对意志力的支撑……
相比之下,教材和AI系统都很“冷”,它们更像是考试机器,缺乏感染力,也缺少人情味。
回到我们的起点:
- 书和讲座的问题一样:它们都没有建立在一个真实的认知模型上;
- 它们隐含的认知模型叫传输主义,也就是“读了就懂了”“听了就会了”;
- 真正能从书中学到东西的人,其实是在靠精巧的元认知技巧,主动调动自己去思考;
- 但这种技能并不普及,而且极其耗神;
- 书并没有真正帮到他们多少;
- 教科书做得稍微好一点,但依然把元认知的重担压给了读者;
- 而且它们忽视了很多关于“人是怎么真正学会东西的”重要因素。
换句话说:书没错,但它们远远还不够。
我们该怎么办?
看到这里,你可能会有个感觉:问题说清楚了,但接下来要走的路实在太陡了。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改进书籍的小尝试,或者一些能辅助读者的工具,但“怎么让书真正有效”这个目标,似乎遥不可及。既然如此,我们不妨反过来问一句:我们爬的这座山,本来就对吗?我们为什么非得爬这座山?
我们前面说过,书这种媒介,并不是围绕“人是如何学习的”这个核心问题而设计出来的。虽然它有“原罪”,但也许通过迭代优化、加上新的阅读辅助工具,书还是可以变得更靠谱的。可也可能,只要我们还被这种媒介固有的思维模式所束缚,我们就永远发现不了真正的突破口。
所以,我想提出一个不太一样的思路:我们不一定非要让“书”变得有效,我们可以直接创造新的媒介形式。
这不等于我们要抛弃叙述性文字,也不一定要放弃纸张。我们要抛弃的,是对“书应该长什么样”的固有想象。也许走完这一圈,我们回过头来发现,新形态其实和书很像;也可能,我们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地形。
换个问法:不是“如何让书真正变得有效”,而是——我们是否能设计出一种新的媒介,它能完成非虚构书籍的使命,而且真的有效?
我承认:这是个研究级的问题,可能得花几代人的时间去探索,不是三言两语能解答的。但我相信它是可能的。现在我想分享一下,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值得相信的方向。
首先要认识到:媒介不是注定的,它是可以被设计的。而且,更重要的是: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种媒介,它本身就蕴含了特定的认知理念。
虽然这个观点听起来有点抽象,但其实早已有无数人实践过。比如:
- 数学证明就是一种媒介,它那种“逐步推进、严密逻辑”的形式,本身就体现了一整套关于推理的理念。
- Snapchat 的 Stories是另一种媒介,它的“24 小时后自动消失”,体现了关于情感与身份认同的深刻洞察。
- 万维网(WWW)也是一种媒介,超链接的设计承载了一个强大理念:知识是关联性的,不是线性的。
有趣的是,这些强大的理念,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。比如你写博客加了个链接,你不会去想“啊,我这是在体现知识的结构认知”。但设计这个系统的人,确实是这么想的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认知原理嵌进了媒介的底层结构里,从而塑造了我们使用这个媒介的方式。
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:“书”这个媒介的问题不只是在于它没有认知模型,更在于它可以拥有一个,甚至可以从这些认知模型里“编织”出来。
好的媒介,不是“传达理念”,而是“长在理念上”。数学证明不是“附带一些逻辑”,而是“逻辑本身的形状”。
那我们能不能反过来问:我们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媒介,它的“纹理”(grain)就天然贴合人类的学习方式?有没有一种媒介,它的默认操作方式,就恰好就是“理解所需要做的事”?
换句话说,有没有一种媒介,让你只要按它本来的方式去“读”,你就已经在做“理解”这件事?
这个问题不小。甚至从理论上讲,我们都还无法精准定义“理解”到底是什么。但我们并非毫无头绪。认知科学已经在这块地图上点亮了不少区域,我们可以从一些关键洞见开始构建。
比如一个关键认知原理是:如果工作记忆被占满,人很难再吸收新信息。
举个例子:你刚接触一堆新术语,结果下一句话里全都出现了,那你大概率啥也读不进去。要理解当前的内容,相关的前置知识不仅要“熟悉”,还得是“内化”的,进入长期记忆的状态。
那我们怎么把东西送进长期记忆呢?
又一个强大的认知工具派上用场:间隔重复(spaced repetition)。
只要你在合适的时间点、通过自我测试,不断复习曾经学过的东西,几乎可以低成本、高效率地把大量信息写入长期记忆。
当然,记忆只是理解的一小部分。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媒介设计的例子:
我们要不要试试看,用“间隔重复 + 降低认知负载”这两个认知理念,去“编织”一种全新的媒介?
我们试着做了一个:Quantum Country
我和 Michael Nielsen 合作,尝试打造了一本关于量子计算的“书”——Quantum Country。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,和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。
它把解释性文字和微型记忆测试紧密交织在一起。你读一小段文字,就立刻进入一次快速回顾练习;然后继续读,可能还会回头复习刚才的内容;接下来几天、几周、几个月里,你的邮箱还会收到一连串基于“间隔重复”的测试题。
这种模式有两个直接好处:
- 减轻认知负担: 到了第二章时,你对第一章的内容已经内化了,理解新的内容变得更轻松;
- 减轻元认知负担: 回顾练习能清晰反馈你“哪学会了、哪没学会”,不需要你自己苦苦监控和判断。
这只是“理解”的一个切片——记忆。但它证明了一个关键思路是可行的:我们可以用认知科学的理念,去“织”出一个媒介。
那我们可以接着问下去:
- 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媒介,让“读者”自然而然地建立起知识之间的深度关联?
- 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媒介,让“读者”自发地与内容产生创造性的互动?
- 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媒介,让“读者”自然地面对、权衡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?
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摆上台面,最终聚合成一个更大胆的问题:
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媒介,让“阅读”这件事本身就等于“理解”?
要彻底回答这个问题,显然不是这篇短文能做到的。但我真心相信:答案存在,而且这些答案,足以让人类知识进化的速度,产生一次新的飞跃。就像最初的书籍革命那样。






